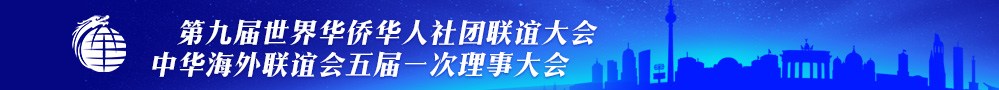可以说,在规矩中形成变化正是“舞人动物纹锦”的纹样特征,而这规矩的排布与局部对称的结构,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“舞人动物纹锦”的问题:织纹最左侧的三角区块中,构成三角区域的矩形部分出现了明显错位(图四),若再进一步比较此区域与整体纹样的中间区域(图五),会发现被称为“对龙2”的纹样中也有不同。而纵观整幅面料还会发现,这一出现在织纹最左侧的错位是随着单位纹样,在面料的经向上完全一致的重复出现的(图六)。
可以说,在规矩中形成变化正是“舞人动物纹锦”的纹样特征,而这规矩的排布与局部对称的结构,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“舞人动物纹锦”的问题:织纹最左侧的三角区块中,构成三角区域的矩形部分出现了明显错位(图四),若再进一步比较此区域与整体纹样的中间区域(图五),会发现被称为“对龙2”的纹样中也有不同。而纵观整幅面料还会发现,这一出现在织纹最左侧的错位是随着单位纹样,在面料的经向上完全一致的重复出现的(图六)。 这样的错织,在今日看来若非考古绘图的一一摹绘,并不容易发现,毕竟织物已暗黄糟朽,但这一“隐藏”的错误,却又是中国古代织造技术得以正名的重要证据。若按照以往学界的猜测,即先秦时期的中国在织造花纹时,是通过手工挑经穿纬而得以交织的话,那么对于织手来说,这种错位的问题即便出现一两次,也应该不会在同一纹样的相同位置不断重复出现,由此来说,从交织技术的角度来看,此“舞人动物纹锦”的织造必然是通过一个预先设定好的、只能机械重复一种“命令”的装置来辅助生产的。
这样的错织,在今日看来若非考古绘图的一一摹绘,并不容易发现,毕竟织物已暗黄糟朽,但这一“隐藏”的错误,却又是中国古代织造技术得以正名的重要证据。若按照以往学界的猜测,即先秦时期的中国在织造花纹时,是通过手工挑经穿纬而得以交织的话,那么对于织手来说,这种错位的问题即便出现一两次,也应该不会在同一纹样的相同位置不断重复出现,由此来说,从交织技术的角度来看,此“舞人动物纹锦”的织造必然是通过一个预先设定好的、只能机械重复一种“命令”的装置来辅助生产的。 从交织原理来说,经锦的交织是用纬线确定色经位置的一种技术形式(图九),判断织物时,有几种色经,我们就会称其为几色经或几重锦。具体织造时,人们会使用综(一组与经线呈垂直排列的,具有承托经线能力的线组,如图一〇),将需要提起的色经统一提拉,在经线组间形成开口(图一一),以便纬线快速通过。每一组与经线垂直的综可以通过联动提经,管理一行色经的显现,但需要在装机时,根据花纹,预先将每一行所需要显现的色经预先安置在综线的岔口之上(图一一)。理论而言,一件经锦织物,其单位纹样依经线方向自下而上由多少行纬线与经线交织而成,那么就需要多少组综来对经线进行管理。
从交织原理来说,经锦的交织是用纬线确定色经位置的一种技术形式(图九),判断织物时,有几种色经,我们就会称其为几色经或几重锦。具体织造时,人们会使用综(一组与经线呈垂直排列的,具有承托经线能力的线组,如图一〇),将需要提起的色经统一提拉,在经线组间形成开口(图一一),以便纬线快速通过。每一组与经线垂直的综可以通过联动提经,管理一行色经的显现,但需要在装机时,根据花纹,预先将每一行所需要显现的色经预先安置在综线的岔口之上(图一一)。理论而言,一件经锦织物,其单位纹样依经线方向自下而上由多少行纬线与经线交织而成,那么就需要多少组综来对经线进行管理。

 “舞人动物纹锦”在《江陵马山一号楚墓》的报告中说它的单位纹样高5.5厘米,且纬密是52根/厘米,也就是说,织造“舞人动物纹锦”的一个单位纹样,需要织纬5.5×52次,即需要286根纬线才能织完一个单位纹样,那么按照织造经锦的综蹑织机逻辑,就是理论上需要装入286组综才能完成一个单位纹样的织造,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(实际织造时,经过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艺传承人王继胜老师研究,可通过排列组合的方式将“舞人动物纹锦”控制在使用110组综进行织造),而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复原的老官山汉式织机上,仅86片综就已经必须分上下两排安置(图一二),且十分拥挤了。
“舞人动物纹锦”在《江陵马山一号楚墓》的报告中说它的单位纹样高5.5厘米,且纬密是52根/厘米,也就是说,织造“舞人动物纹锦”的一个单位纹样,需要织纬5.5×52次,即需要286根纬线才能织完一个单位纹样,那么按照织造经锦的综蹑织机逻辑,就是理论上需要装入286组综才能完成一个单位纹样的织造,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(实际织造时,经过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艺传承人王继胜老师研究,可通过排列组合的方式将“舞人动物纹锦”控制在使用110组综进行织造),而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复原的老官山汉式织机上,仅86片综就已经必须分上下两排安置(图一二),且十分拥挤了。 “舞人动物纹锦”的错位,是在织机装造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,穿综时,对“龙纹2”右侧龙尾到前肢部分的色经被并排穿引了两次,因此最终形成了织造时的错位,但若要调整这一问题,按照“舞人动物纹锦”156根/厘米的经密及其三重锦的结构来看,虽然错位部分仅占整个单位纹样的2%,但重新穿综数却不少于3000次。相较于其相对不明显的错位而言,重新装机的耗费太大,或许这也是“舞人动物纹锦”最终以错织面貌出现的根由。
“舞人动物纹锦”的错位,是在织机装造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,穿综时,对“龙纹2”右侧龙尾到前肢部分的色经被并排穿引了两次,因此最终形成了织造时的错位,但若要调整这一问题,按照“舞人动物纹锦”156根/厘米的经密及其三重锦的结构来看,虽然错位部分仅占整个单位纹样的2%,但重新穿综数却不少于3000次。相较于其相对不明显的错位而言,重新装机的耗费太大,或许这也是“舞人动物纹锦”最终以错织面貌出现的根由。 再看单位纹样最高的绣纹,此绣纹见于N7对凤对龙纹绣浅黄绢面衾上(图一四),绣纹单位纹样宽22厘米高181厘米,由八组单脚独立的龙或凤沿面料纵向排布(图一五),每一组的龙或凤的高度均有20厘米左右,而再反观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的交织物,其中花纹经向跨度最大是一件残高12.4厘米的大菱纹锦B型(从织造技术的角度而言,此大菱纹锦花纹上下对称,因此实际织造时,有效的单位纹样只需6.2厘米左右即可),若依照大菱纹锦(B型)的纹样尺寸去对比,凤鸟的形象大约只能出现半只左右(图一六)。
再看单位纹样最高的绣纹,此绣纹见于N7对凤对龙纹绣浅黄绢面衾上(图一四),绣纹单位纹样宽22厘米高181厘米,由八组单脚独立的龙或凤沿面料纵向排布(图一五),每一组的龙或凤的高度均有20厘米左右,而再反观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的交织物,其中花纹经向跨度最大是一件残高12.4厘米的大菱纹锦B型(从织造技术的角度而言,此大菱纹锦花纹上下对称,因此实际织造时,有效的单位纹样只需6.2厘米左右即可),若依照大菱纹锦(B型)的纹样尺寸去对比,凤鸟的形象大约只能出现半只左右(图一六)。

 而若想仅用一件绣品就了解江陵马山一号楚墓的刺绣神韵,N2蟠龙飞凤纹绣浅黄绢面衾(图一七)应该就是最好的选择了,此衾上的“盘龙飞凤”纹,单位纹样高72厘米、宽44厘米,绣线虽仅用棕、深红、土黄、浅黄4色,却搭配出富丽大气的装饰效果(图一八),让人不禁想问,既然4色都可以配出如此绚丽的效果,为何江陵马山一号楚墓的织物却只用3种颜色就“满足”了呢?
而若想仅用一件绣品就了解江陵马山一号楚墓的刺绣神韵,N2蟠龙飞凤纹绣浅黄绢面衾(图一七)应该就是最好的选择了,此衾上的“盘龙飞凤”纹,单位纹样高72厘米、宽44厘米,绣线虽仅用棕、深红、土黄、浅黄4色,却搭配出富丽大气的装饰效果(图一八),让人不禁想问,既然4色都可以配出如此绚丽的效果,为何江陵马山一号楚墓的织物却只用3种颜色就“满足”了呢?
 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在经锦技术的发展之中,前文已经提到,经锦的织造需要预先绷拉经线,且每增加一色,就需多预备一组经线,应是出于材料或者综框条件的限制,战国楚地的交织尚无法支持4色经线的织造,当然也有可能是现有文物中并没有出现更高级别的楚时遗存,故而无法得见楚地的4色经锦。不过在不久之后的汉代,东汉文字锦等实证都已向我们证明,经锦织物的色彩问题,在那时已得到解决。
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在经锦技术的发展之中,前文已经提到,经锦的织造需要预先绷拉经线,且每增加一色,就需多预备一组经线,应是出于材料或者综框条件的限制,战国楚地的交织尚无法支持4色经线的织造,当然也有可能是现有文物中并没有出现更高级别的楚时遗存,故而无法得见楚地的4色经锦。不过在不久之后的汉代,东汉文字锦等实证都已向我们证明,经锦织物的色彩问题,在那时已得到解决。


 秦统一天下,楚地风华终隐没于大一统的庄严之中,即便是刺绣似乎也难再有那洒脱与奔放的楚地风姿(图二三、图二四)。交织也因受到技术的局限,而长期处于“制式化”的阶段,不是一条条的横向条纹,就是在对一个单位图案的不断重复(图二五、图二六)。
秦统一天下,楚地风华终隐没于大一统的庄严之中,即便是刺绣似乎也难再有那洒脱与奔放的楚地风姿(图二三、图二四)。交织也因受到技术的局限,而长期处于“制式化”的阶段,不是一条条的横向条纹,就是在对一个单位图案的不断重复(图二五、图二六)。
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探索之后,我们从最初的只能表现几何纹样(图二七),到能够织就各种具象形式(图二八),人类交织世界的缩影都在古代中国一幕幕地上演了。
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探索之后,我们从最初的只能表现几何纹样(图二七),到能够织就各种具象形式(图二八),人类交织世界的缩影都在古代中国一幕幕地上演了。
 动物、植物与人,抽象、具象与夸张,人们认识世界,又进一步构建自身的文明,这有形的纹章与无形的文化最终都在交织的世界凝固、存留。
动物、植物与人,抽象、具象与夸张,人们认识世界,又进一步构建自身的文明,这有形的纹章与无形的文化最终都在交织的世界凝固、存留。